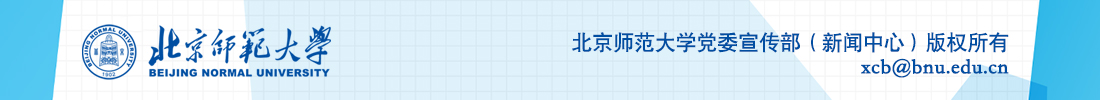编者按:赵峥,我校物理学系教授,中国引力与相对论天体物理学会理事长。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师从诺贝尔奖得主普利高津教授获博士学位。赵峥长期从事理论物理的教学与研究,在黑洞热性质、时空奇点、钟速同步和热力学的关系等方面有创新性的工作。他热心从事科普工作,向社会各界宣传普及物理学基础与前沿知识,科普著作两获中国图书奖。本期起,我们将一起探访赵峥教授与物理学的不解情缘。

(一) 少年故事
我是1943年8月在四川成都出生的。我父亲是江西萍乡人,母亲是山西榆次常家大院的人。我们一家人因抗日战争的原因从山西迁到了四川成都。当时,父亲是四川大学的毕业生。1949年解放后,北方大学招人,我们全家先到张家口,后又至北京。我的小学在成都、张家口、北京都上过,中学是在北京一中读的。
小学时,我成绩不是很好,记得在张家口时,全班46人,我是第43名。到北京后,考五年级,我还没考上,结果留了一级,又上了一次四年级,这次失败的经历对自己影响很大。重读这一年,我的知识基础打得比较好。当时学校的条件很差,学生也不多,上五年级后,两个小班还合成了一个班,总共只有10个男生。我在五年级时竟然得了七、八个2分,包括历史、自然等科目。还记得期末考试,历史有一道题是问“国家是怎么产生的?”我答不出来,结果得了2分。转学时找班主任办手续,她一边给我拿成绩册,一边对别的老师说,“我们班的几个好学生都要走了。”我一直很诧异,不知道她怎么看出我是个好学生的。
转学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那时候有一个美术老师对我很好,一直鼓励我,我的成绩开始慢慢变好。升初中的时候没有考上北京四中,到了北京一中。反思这段经历,觉得这对自己反而很有利。在这个中等的学校里,自己逐渐成了尖子生,学习主动,有大量空闲时间,过了一段自由自在的日子。
当时因为北京一中扩招,教室不够,故采用了二部制授课,每天只上半天课。因此有了大量的自由时间。等到初三,我自觉到应该努力,开始制定计划,努力学习。我从初三开始就有了给自己定计划的习惯,这个习惯没有任何人引导,因为家里也不注重我的考试成绩。后来成绩开始突出,但自己却没有意识到,直到老师要求班上同学向我学习时,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为班上的尖子生。中考时,我被保送上本校高中。高中因为成绩一直很领先,压力不大,因此有余力做一些其他工作,做了班长、团支书等。又加上赶上困难时期,吃不饱,学校规定每天睡十二个小时保存体力,我利用这段时间看了很多书。
我从四年级开始看《水浒传》,这本书后来成为影响自己最大的书之一,我个人很佩服那种为了公平正义,说公道话,拔刀相助的精神,通常比较同情群众。在上初中时,除《红楼梦》之外,古典小说中的名著大部分我都已经看过了,这对自己的古文阅读有很大帮助,高中看的课外书主要是科普书。尤其《原子核能》、《少年天文学家》、《每月之星》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京一中的图书馆历史比较悠久,藏书丰富,给了我更多的阅读机会。于是在高中度过了两年多的“神仙生活”:一是有大量空闲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二是肚子经常有饥饿感,很像那些云游的和尚与道士。在多数人关心营养和饥饿问题时,我自己却转移注意力,把精力放在看书上,收获很大。
对科学产生兴趣的原因是五六十年代“火星大冲”(太阳、地球和火星位于同一条经线上,这一天文现象称为“冲日”,简称“冲”;火星在近日距时发生的“冲”则称为“大冲”;广东天文学会的专家认为,每隔79年,就会发生一次罕见的火星大冲),自己又恰好在同学家通过望远镜看到过火星,因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想当一名科学家。但关于如何成为一名科学家自己并没有想法。
解放初期那几年自然灾害的现实情况,进一步坚定了我做科学家的想法:我当时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苏联专家撤走造成的。因此自己暗自下决心,要努力成为中国自己的专家,为祖国做贡献。
高中期间我参加了兴趣小组,当时是在化学组,我还经常去听北大的教授讲化学课。这期间我对周期率产生了兴趣,非常佩服门捷列夫,他居然能从杂乱无章的元素中找到一个如此漂亮的规律。青少年时代我非常关注天文学和原子能,当时对化学、天文、物理都感兴趣。
记得当时的中学课程中政治教育的内容比较多,自己受的影响比较大,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思想就是那时候扎根于心的。我偏爱历史,只要是历史我都喜欢。比如说古代的,中国的历史,西方的历史。近现代史方面,如果要我讲朝鲜战争,肯定一般学朝鲜战争史的人都讲不了像我那样生动。因为我知道很多细节。我可以讲大家感兴趣的,比如讲二战,我可以一连讲好几天。二战从开始到结束,是怎样一步一步打的。我对来龙去脉了如指掌,所以我根本不相信西方的说辞,他们总是强调美国和英国是主力。其实主力是苏联,美国起了很大作用,这是肯定的。但是德国军队主要是苏联歼灭的,而日本和意大利的力量比德国差远了,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美国人说俘虏了一二百万德国军队,那时德国军队已经战败,他们投降苏联没有好处,苏联人要报复他们——他们在苏联杀了那么多人,毁了那么多城市,所以都往西方跑,见到英国人、美国人就投降。另外苏联人也吹,说他们消灭了多少关东军,也有这个关系,那时日本人也不行了。日本军队也想,我与其向中国军队、美国军队投降,不如向苏联军队投降,因为他们给苏联没造成什么大的危害。
那时候,我对物理方面也有一定的兴趣。特别是困难时期,我看了很多书以后,心中有了自己的想法。我感受到,为什么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去自己制造,要依靠别人呢?那时的青年学生都很爱国,都想着怎么把科学技术搞上去。学习的时候心里都攒着一股劲,都是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的。
有时候我想,假如我的少年时代是和平富足的时代,我大概会学历史。当然也很难说,学到后面,说不定发现什么更感兴趣的。因为像我们家的环境,虽然父母亲钱挣的不是很多,但还是属于比较宽裕的,家里也不要求我做家务,不要求我打工,我可以集中时间看书。我父母是教师,教师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在家备课,家里有读书的气氛。如果家里成天打麻将,那不就一团糟了?那时家里也没电视,完全是安静的读书环境。父母给我的影响是很敬业,但对科学研究知道不多,对子女的教育也比较随意。总之在家中比较自由,爱看书的习惯是受到了家庭氛围的影响。
(二) 结缘师大
进入中科大学习,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之一。当时有好几所大学做招生宣传。北大、清华、科大我都考虑过。我还去了北大物理系参观他们的实验室。但当时科大招生宣传是由钱三强、华罗庚等科学家做报告。我听了钱三强先生的报告后,备受鼓舞,就下定决心考科大了。
1962年的高考非常公正,基本上不看政治条件,分数是唯一标准,我如愿考取了科大。科大在当时师资力量不如北大、清华。北大、清华都是长期积累的,而科大1958年才成立,当时临时从中科院各研究所,以及大学刚毕业的学生里抽了一批人当老师。但科大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由最好的老师讲基础课,由院士(学部委员)们亲自给学生讲课。像华罗庚先生就给数学系一年级学生讲高等数学,严济慈、钱临照院士给各系讲普通物理。这一做法给我深刻影响,到师大工作后我也一直认为应该重视大一、大二的基础课,基础打好了,以后就不会有很大问题了!
在大学阶段,国家的经济状况在不断好转,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前三年的大学生活过得很充实。科大的学生都很拼命,大家学习都很努力。当时科大的主楼日夜灯火通明,有时开夜车的还没走,开早车的就来了。所以在当时的北京中学生间就流传一句话:“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这话我是深有体会的。
大学前三年,我除了参与政治活动、体育锻炼这些不可避免的事之外,其余所有的时间都扑在书上了。假期大多数人不回家,一是因为有的同学家境困难,来回火车票虽是半价但也舍不得,再一个就是想在假期看看书,那看什么呢?有的同学就看学过的书,去复习。我觉得自己数学不怎么好,科大的数学学得很难,考试题更难。我问一位上海来的同学,你都怎么学数学的啊?他说你光看课本有什么用啊,你得看费赫金哥尔茨的《微积分学教程》,做吉米多维奇的《数学分析习题集》上的题。我当时就照做了,第一个假期我看完了《微积分学教程》第一卷,后来我又用了大概四五个假期看完了《微积分学教程》八册中的五册。但实际上连莫斯科大学数学系都不要求看完,他们也只是看简写本《数学分析原理》。除了数学外,另外我还看了很多相对论的书。那时找不到一个懂广义相对论的人,我就利用假期买书自学,每天上午、下午、晚上分别看三种书:物理、数学、还有就是马列主义。那时我就读了坦盖里尼写的《广义相对论导论》,还看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意义》和柏格曼著的《相对论引论》的一部分。虽然没有读懂,但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政治书籍如《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很多原著当时我都看过。
后来接触相对论领域是在中科院相对论小组。当时湖南的一个教师做了一个摆锤实验,提出一些猜测结论,引起一些争论。于是中科院成立了一个研究相对论的小组,组织中科院物理所、化学所、天文台及科大、清华、北大的一些人参与研究。当时正值“文革”期间,老先生们都受到冲击,所以各单位去的人都是年轻科研人员和学生。因为对相对论有兴趣,科大选了我与朱清时(后来曾任科大校长)两个学生去,但是我只待了不到两个月,就因为政治原因提前离开了,后来朱清时也离开了。这个小组后来演变成批判相对论的小组,再后来又演变成今天中科院的理论物理研究所。虽然我对批相对论没有兴趣,但是因为可以得到一个合法的读相对论书籍的机会,还是很高兴的。
大学前三年的基础课我学得非常扎实,到四年级开始分专业,我分在激光专业,这是全国第一个激光专业。当时是由中科院物理所和半导体所负责科大的物理系,钱临照院士主持教学工作。很多课都由钱临照先生亲自上或亲自安排,基础课是严济慈先生上,当时关肇直、吴文俊等先生也都在上基础课和专业课。
后来国家形势好转,但与苏联关系恶化,我自己有了更深的责任感,想为中国的科学工作做贡献,很希望从事更重要的工作,但因为政治原因也没有机会。
其实我仅仅上了三年的课,四年级搞了一年的“四清”,接着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但是此前我上的三年的课非常重要,我现在很多的东西都是依靠当时那三年的基础。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我们没有学完本科课程的机会。希望现在的学生能够珍视机会,大学四年能够扎扎实实地学习。
1967年我大学毕业。由于“文革”毕业分配拖了一年,1968年才正式分配。我被分配到中科院的一个研究所———哈尔滨石油化学研究所。结果去之前又让我在部队农场劳动了一年多。因此,我从大四开始,一年“四清”、两年“文革”、劳动两年,前后五年完全脱离自然科学。到了研究所干的也不是我学的东西,因为是化学研究所。我在那里搞的是X光衍射实验,研究催化剂等等。后来研究所希望我学核磁共振,就派我来师大物理系学习。那是我第一次到师大听课,也没有想到后来竟会来这里工作。
我回所之后,就想着考研究生。我最初是想考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也曾打算考科大,但是它南迁到合肥去了。后来看到北师大也在招相对论专业的研究生,我就写信把我的两篇稿子寄过去了,一篇是写马赫原理的,另一篇是关于宇宙学红移的。天文系老师回信欢迎我来,我就决定考师大天文系的研究生。当时师大天文系是全国仅有的两个天文系之一,另外一个在南京大学。考试我没有特别重视,指定的参考书我认为比较简单,也没下功夫复习。结果高等数学考的都是技巧问题,考得很糟糕。第二天考量子力学和电动力学,开始一看八道题一个也不会,但是想想总不能交白卷吧,于是就在那坐着,后来一看,第八道会做!第七道也会,最后就把八道题倒着给做出来了。
最后我就靠着量子力学和电动力学把总分给提上去了,复试时刘辽先生对我十分满意,当场拍板要我,于是就考进了北师大。当时北师大天文系只招了两个相对论的研究生,都是刘辽先生带的。我三年的研究生课程都是和物理系的研究生一起上。当时学生都很努力,都很珍惜文革后来之不易的稳定环境和学习机会。因为我在研究所已经开始搞科研了,有一定的科研经验,但相对论研究还是刘辽先生把我领进门的,基础是他帮我打好的,最初的课题也是他帮我选的。我在研究生二年级时开始发表论文,在刘先生的带领下逐渐钻研进去,进入科学研究的领域。后来又一直得到他的指点。在硕士研究生期间我搞的研究比较多,一共做过十二个研究题目,成功了六个,发了六篇论文。
毕业之后我留在了物理系工作,一方面继续搞黑洞相关的研究,另一方面,跟着老教授听了两年课后,就开始讲课了。师大老师讲课非常认真,特别清楚,刘辽、喀兴林、梁绍荣、高尚惠、梁灿彬等老师讲的课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后来的教学工作很受他们的影响。总结自己的特长主要是基础较扎实,物理图象清晰、想象力比较丰富,而且具有跳跃思维,容易找到题目。
(三) 师恩难忘
我从1978年开始进入北师大相对论研究团队。这个团队为相对论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文革”之前,中国只有零星的相对论研究,没有形成气候。“文革”期间,一些初级的相对论探讨在混乱中出现。真正的相对论研究是从“文革”后开始的。当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神州大地的时候,一些在严寒压抑下顽强生存的相对论探索者,开始出来宣传、普及这一理论,并逐步展开了合法的研究活动。以刘辽先生为首的北师大相对论小组,是当时三个最重要的研究和普及相对论的团队之一(另外两个分别在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技大学)。
刘辽先生祖籍湖南湘潭,1928年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刘辽先生的父亲刘朴是著名的中文教授,上世纪20年代后期应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将军之邀,到该校任教。其时,日寇亡我之心已昭然若揭,刘朴教授悲愤之至,为自己新生的四子起名为“辽”,字“子复”(给他三哥起名为“沈”,字“子恢”),意在恢复辽沈。强烈的爱国之心又促使刘朴教授写了一篇《过辽论》,揭露日本鬼子与汉奸亡我中华的阴谋。这篇论文当时流传颇广,影响很大,因而受到日本鬼子的注意,把刘朴教授视为眼中钉。于是,刘朴教授不得不于“9•18事变”前夕举家迁往关内,以躲避日寇、汉奸的迫害。
1947年,刘辽先生在重庆上中学时,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极为反感,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地下活动,秘密散发《挺进报》。正当他填写入党申请书时,川东地下党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发现,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刘辽的名字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幸亏在此之前他已离开四川,于1948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在北平,刘辽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他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游行活动,监视一些特务学生的行踪,反对国民党政府南迁北京大学的阴谋,满腔热情迎来了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后,“民青联盟”成员本可自动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但刘辽觉得革命已经完成,以后主要任务是科学技术救国。因此他没有转团,而是把自己的热情投入到学习中。
1956年,刘辽先生调到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工作。不久整风运动、“反右”斗争在全国展开。刘辽也被卷入了洪流之中,“右派”这顶帽子,他一戴就是十八年。此后,政治运动不断升级,刘辽先生被反复批判、劳改,他和家属长期受到极大的政治压力和各种歧视。但是,刘辽先生没有被巨大的压力所压垮。他利用劳动之余努力钻研科学著作,特别是广义相对论,坚韧地希望凭一己之力进入科研领域。在劳改之余学习理论物理,在黑暗中形成了师大最初的相对论小组。改革开放之后,刻苦钻研相对论近20年的刘辽先生成为了广义相对论的积极传播者和科研专家。他走出校门,到处讲学,形成了桃李满天下的局面,当时全国研究相对论的人,约有三分之一直接或间接出自他的门下。
80年代初,北师大相对论小组的梁灿彬先生赴美国追随国际著名相对论专家瓦尔德(R.Wald)和杰拉奇(R.Geroch)学习广义相对论,把用整体微分几何表述的现代广义相对论形式引进中国。梁灿彬先生把大量精力投入现代微分几何与广义相对论的教学与传播,为推动中国的相对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北师大相对论小组对中国相对论事业做出的第二波贡献。“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曾连续听了梁灿彬先生好几个学期的讲座,有关知识对我后来的科研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追随刘辽先生主要从事两方面的研究,一是黑洞,二是时间的性质。他直接指导我进入了黑洞量子热效应的研究和引力波的研究。他的讲义中介绍了著名物理学家朗道关于“同时传递性”的工作,一般相对论书籍和文献都不涉及这一重要问题,它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在此后的若干年中,在发表大量黑洞热性质论文的同时,我一直断断续续地思考“同时性”问题,思考时间能否定义的问题。
1985年,我出国去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深造,遇到了我人生中的另外一位重要老师———诺贝尔奖得主普利高津教授。
普利高津教授对中国十分友好。早在1979年就曾来我国参加“第一届全国非平衡统计物理学术会议”。他多次邀请我国学者到他领导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索尔维国际理论物理和理论化学研究所,及美国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统计力学和热力学研究中心去工作、进修、访问,并经常与我国有关单位交换学术资料,交流彼此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在非平衡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方面的研究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对政治普利高津从不直接涉及,但他很希望全世界的老百姓都和谐相处。比如说,在他的研究所里有中国、印度等好多个国家的学生,我跟一个印度学者处得比较好,他很满意;如果不同国籍的人闹意见,他就不太高兴,他觉得不应分民族种族。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学术活动比较多,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讲座,图书资料也非常全,让我很受益。
在一般人看来普利高津早已功成名就,当时年逾花甲的他应该享享清福才对,但他一直非常勤奋,假期也经常在办公室里工作。他每天的工作计划安排得满满的。要见他的人或他要见的人都事先通过秘书约定时间,往往因为前一件工作拖延而把约见的时间推后。有一次他让我第二天下午去见他,我提醒他第二天是法定假日,他说他知道,他会在办公室等我。
在我心目中,普利高津是个帅才。他对什么都感兴趣,他手下一些人看不惯他这一点,说他什么都研究,其实我觉得这才是帅才的表现,其他人都不如他。他对统计物理,对宇宙演化,对量子理论,对历史都感兴趣。他最感兴趣的东西是“时间箭头”,是时间方向性和流逝性(即不可逆性)的根源。他曾推测宏观不可逆性源于微观不稳定性,在这方面花过很多时间。他曾几次对我谈到宇宙演化中的熵变化问题。那段时间我看了许多非平衡统计的资料,对相对论性的非平衡统计理论做过一些探讨,花了不少时间思考“时间箭头”问题,但都没有取得重要突破。不过,有关探索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时间”问题的兴趣,使我认识到“时间”问题远比“空间”问题来得复杂,内涵也更为丰富。
此后,对“黑洞”和“时间性质”的研究伴随了我的几乎全部科研生活。我一方面继续开展黑洞量子热效应和信息守恒问题的探讨,一方面对时间的定义、时间有无开始和结束,以及时间的流逝性等问题进行思考。我一直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对得起几位导师对我的培养。
(四) 青年是科学发现的主力军
我长期从事理论物理的研究与教学,特别是相对论、黑洞和宇宙演化方面的研究与教学,也经常对文、理、工、农、医各专业的学生做科普讲座。在与学生的接触中,深感如果能够让年轻人了解自然科学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了解人类文明在宇宙演化中的位置,会大大开阔他们的眼界,提高他们学习的兴趣。而兴趣是产生天才和动力的最重要的源泉。
实际上,自然科学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是文明与社会进步的催化剂。科学与文明是分不开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也是相通的。目前的教学体制过早地把学生分为文科和理科,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割裂开来,绝对无助于年轻人综合素质的发展,无助于优秀人才特别是杰出人才的涌现。
在过去的数百年里,物理学对文明和社会的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让年轻人特别是学习文科的大学生了解物理学最重要的思想、内容和方法,以及物理学与人类文明的关系,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事情。我想在这方面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因此,我写了一些物理学的科普读物,包括《探求上帝的秘密》、《物理学与人类文明》、《黑洞与弯曲的时空》、《物理学与人类文明十六讲》、《相对论百问》等书。希望通过这些通俗的物理学科普读物,使各专业学生能在避开繁杂数学计算的、较为轻松的情况下,掌握深奥理论的主要思想,了解科学发现的曲折历程,学到科学研究的方法。
纵观500年的自然科学史,青年是科学发现的主力。伽利略25岁被誉为“当代的阿基米德”。牛顿23至25岁期间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科学发现。莱布尼兹27岁发明微积分,伽罗华20岁创造了群论。赫姆霍兹26岁、迈耶28岁时提出了热力学第一定律。克劳修斯26岁时提出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开尔文24岁提出绝对温标,并预见到热力学第三定律的存在。麦克斯韦25岁对电磁理论作出重大改进,34岁建立起著名的电磁方程组。爱因斯坦26岁发表狭义相对论,提出光子说,36岁又发表广义相对论。历史上重大的科学发现,大多是年轻人做出来的。他们虽然知识不如老年人丰富,但很少保守思想,最具创新精神。
现如今,很多欧美国家的教授对中国学生的考试能力普遍感到钦佩,但觉得中国学生的科研能力远不如考试能力那样出色。这反映了中国学校教学成功的一面和失败的另一面。一般说来,中国学校普遍强调刻苦学习、强调基本功、强调做练习,中国学生投入的力量和时间远非欧美学生可比。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中国学生动手做实验的机会远比欧美学生少。而且,在教学过程中,中国的老师往往不注意突出科学思想和探究精神,不注意让学生了解科学发现的艰难过程,不注意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方法和兴趣,这就造成了中国学生“考试见长、科研见短”的“奇特局面”。
建议大家了解一下索末菲的“人才特别快车”,玻恩在哥丁根大学的研讨班以及玻尔在哥本哈根领导的理论物理所,读一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和《居里夫人传》这两本书,你们会从中悟出成才之路。
同学们要相信自己的实力,抓紧时间,努力进步。我们北师大在实力上可能弱于北大和清华,但在全国范围内,绝对是排在第一个档次的。所以希望同学们要有信心,要有做大贡献的志向。正如拿破仑所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
搞科研首先应该“追”一个好的导师,跟着他走到比较高的地方,这样科研的起点就会比较高。如果一开始没有做出好的工作也没有关系。刘辽先生对我说过,科研是一代一代人像阶梯一样爬上去的,不可能一下子就上去。年轻人可以看一些课外读物、科普书和科普杂志,扩大知识面,从中潜移默化地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近代以来,我们国家在自然科学上缺少独创的东西。不少人强调逻辑推导,其实按逻辑推导出来的东西都不会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著名的物理学家福克说过:科学上天才的、甚至不仅是天才的发现,都不是靠逻辑推理推导出来的,而是猜出来的。
同学们应该多了解一些“活的”科学史,而不是教条式的、“死的”科学史。科学史教育不应是简单地抽象地阐述人物简介、经济背景以及社会背景,而应该通过一些真实的故事让学生体会:科学家是怎么成才的,怎么思考的,如何提出问题的,遇到困难是如何克服的,他们如何面对失败和成功。让同学们了解到科学家重大发现的背后经历过怎样的失败和磨难,从而不再神化科学家,让学生们看到真实的科学家是人不是神,并非高不可攀。这样一来,大家也就不会觉得科学是高深莫测的东西,对科学研究也就敢想敢干了。思想上要敢于大胆创新,猜错了也不要紧,不敢猜不敢闯才是大问题。
我们北师大的学生可能自信心不太强,缺乏北大清华学生那种“狂”劲。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年轻时就有点“狂”,没把别人看成是我赶不上的。其实我们师大的同学基础都不错,应该有自信心。
翻开历史的长卷,我们看到“自古英雄出少年”。青年人应该有志气,有抱负,完全不应在权威面前有自卑心理。应该像牛顿那样,努力站在巨人的肩上,让青春发出光辉。青春的光辉,主要产生于勤奋而不是天才。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在天才和勤奋之间,我毫不迟疑地选择勤奋。它几乎是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催生婆”。所以青年人一定要勤奋。一些科学家出身于名门望族,但更多的科学家出身于普通家庭,许多还出身于贫困之家。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出身平民,他曾对那些贵族纨绔子弟说:“我没有显赫的门第,但是我的门第将因为我而显赫”。贫贱往往成为人们奋发图强的强大动力。蒲松龄也曾用下面的对联自勉自警:“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最后,我想用清代诗人赵翼的两句诗来结束本文:“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