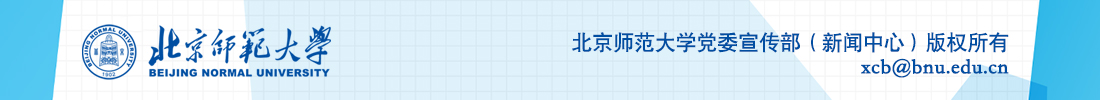她的兄长,是将《红楼梦》、《鲁迅文集》等上百部中国文学作品推向世界的翻译大家杨宪益;她的丈夫,是指导过我国第一部超远程雷达和第一代系列计算机研制工作的两院院士罗霈霖;她师从于中国近代知名学者、诗坛巨匠顾随;被誉为李清照之后诗歌理论及诗歌创作女领军的叶嘉莹是她的同门师妹……杨敏如,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在一连串辉煌光影的簇拥之下浮现在我们面前。然而,笼罩在光晕中的杨敏如,却时刻不曾黯淡了她自身的璀璨。六十余载躬耕教坛,化育英才桃李绚烂, “九十得意是教书”的杨敏如先生,正以她自己的方式,创作着为师者深婉浏亮的辞章。

我这平凡而又充实的一生(上)
我的这一生,没有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做老师,从重庆到天津,从天津到北京,从南开中学到北京师范大学,伴随着中国政治的风起云涌,我的教学生涯也一路跌宕。今年的教师节,我家的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来自国外的牵挂,回荡在北京的慰问,间歇传来的外地的祝福……教学六十余年,我的学生如此之多,如今散布在每一个他们默默奉献着的地方。但是,不管身在哪里,不管是否已是花甲之年,他们依然记得向我道声节日快乐,身体安康。于是,回顾我这平凡而充实的一生,我想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题记
风雨飘摇未名湖畔
我的祖籍在安徽泗州,现在这个地方已经不存在了。祖上做过大官,父亲在天津任中国银行经理。1916年我出生在天津,父亲于1919年逝世,留下三个母亲,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还有富裕的遗产。他把一家子都托付给我的叔叔。嫡母管家,我的母亲因为生了儿子,又和父亲度过了六年的甜蜜生活,所以她分到了几万元股票作为财产。没过几年,叔叔用了我们的财产,房子也卖了,大家庭散了,三姐出嫁了,二姐死了,只留下嫡母,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住在出租的房子里。
我的生活应该从入北京私立燕京大学开始讲起。1934年,我十八岁,来到到处呈现大自然之美和古老文化气息的北京,进入私立燕京大学读中文系。第一使我惊喜莫名的是这今古交融、中西合璧的校园。那堂皇宫殿似的建筑:一对石狮守护着厚重大门,迎面是蓝空下的白玉华表。巍峨鼎立的是贝公、穆、睿三座教学楼。向右深入,则见庄严的图书馆,玲珑的姊妹楼。在佳木葱茏、芳草如茵中,较远卓然独立的是适楼,较高龟驮石碑处有钟亭,旁侧有大体育馆和琴室,呵护着作为女生宿舍的两两相对的四个院落。但这一切都比不上潇洒的临湖轩以东的未名湖一片碧波清水,那湖光塔影,岛亭柳岸,可称燕园胜景之最。第一次瞥见它,它便使我感受到只有在母亲怀中才有的温暖和安谧,我向它注目,它绽开笑容,似乎说:“新同学,欢迎你,这里将是你四年的新家!”
大学的学习生活非常繁忙,但是课程我们都非常喜欢。老师们讲着他们正在研究的题目,或买到什么宝贝的书等,我们如坐春风,贪婪地聆听他们的高论,这里学术风气开放而自由。研究生吴世昌高谈阔论,他在批评胡适;陈梦家在讲文字、音韵,而我却只知他是新月派诗人;更有一次,主任郭绍虞把我们聚在未名湖的岛亭上,聆赏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谷音社来唱昆曲。清华大学中文系俞平伯、朱自清、浦江清等名教授平时都还没见过,听他们唱,真是如听仙乐。郭绍虞见我喜爱昆曲,便常邀我去他家,他按风琴,我和师母、大妹唱着玩。曾请到杨荫浏先生为我们排《出塞》,有趣的是不用工尺谱,而用五线谱。
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我的学业被中断了半年。半年后恢复上课,来到悬挂美国国旗的燕大,校园宛然,师生依旧,春天的桃花、李花开着,钟亭的钟声响着,但是,风雨如磐,山河破碎,未名湖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燕园失去了往日的生气。“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秦少游的词正说明我的心境。
热血投奔南开中学
最后一年半的大学生活就这样黯淡地过去了。1939年我从燕京大学毕业后一直想找一条安全的去大后方的道路,这时系主任建议我考研究生。当时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之间有合作关系,在燕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的学生很容易去美国哈佛留学,这看起来也是一条很辉煌的道路。但是就在我读研究生半年之时,我悄然地离开了学校,去了抗战的大后方。七七事变之后,许多同学都离开学校,去了后方宣传抗战,他们经常给我来信,字里行间阐释着革命的理想和抱负,他们正走在时代的前列,接受着炮火的洗礼。妹妹有一次来信问我:“你还要在灰色的北京待多久?”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抗日。什么是自由?当时的燕园已没有自由。怎样去服务?我要到后方去教书,才能为年轻的同胞服务!
当时哥哥还在英国牛津,已经读了六年的硕士,并为了不在英皇像前屈膝而放弃了继续读博士。妹妹远在西南联大,妈妈身边只有我一个。不管我去哪里,都不能丢下母亲。于是和母亲商量好了,在暗暗寻找了很多机会后,1939年寒假,我和母亲终于通过叔叔的一点关系经香港转到了革命的后方重庆。凭借在燕京大学学到的知识,我在重庆顺利成为南开中学的一名老师。教育救国,这便是我以老师为职业最初的一个抱负——我要教书,像我的老师那样教书!
虽然战乱辛苦,我也要赚钱养活自己和妈妈,但是能够做一份对抗战有意义的工作,这对于我来说是莫大的幸福,我也用更多的心思投入到教学之中。我进入南开中学的头两年教的是英文,后来才改为教文学。南开中学曾经办过一个实验班,学生都是初一十二三岁的孩子,规定老师必须全英文讲课,看着那群天真活泼的孩子,我是发自内心的爱啊!我怀着几分忐忑之心,边说英文边用动作比划教他们,后来竟然成功了,两年的时间学生们英文进展得飞快。当年的这些学生后来个个都有不菲的成绩,当有人问他们英语怎么说得如此之好,他们总是会说,是当年杨先生给我们打的、 郗基础好。我听到这些,思维就能立即飞回到南开中学的教室内,学生们正跟着我认真地朗读……一切仿佛仍在眼前!
在大学里学的昆曲这时也派上了用场。那时中央大学词曲教授唐圭璋正在南中教课,谷音社也在南中有活动。我们纠集一些爱好昆曲的同事,每周末在我家学唱昆曲,时间一长,名扬于外,颇有一些名人闻声而至,如胡小石、卢冀野、吴白匋、张充和、章元善等,无不引吭高歌。一声“漫拭英雄泪”(《山门》),正好宣泄一下对残暴的日军和乌烟瘴气的国民党政府的积愤。以后我在南中教高中国文。他们的课本,高二的是韵文史,高三的是子书。我努力在图书馆备课,为我后来的讲课奠定了基础。
在南开中学一待就是七年半,直到抗战取得胜利,我才和先生罗霈霖回到天津。七年半的教书方知当年在燕大读书生活之可贵。学与教正是人生的攀登之路,也是我这一辈子的黄金年代。1945年抗战胜利,1947年复员返津,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才被调到北京,终于在以后的校友节中,我才得以重见久别的未名湖。
我这平凡而又充实的一生(下)
九十圆梦师大校园
1945年我的老伴从国外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工作,我也从天津师范大学转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这时新中国的旗帜已经高高飘扬,水深火热的烽火岁月也成为了历史。我继续做老师,除了教授知识也想把更多做人的道理传授给学生。就这样我在师大一待就是30多年,直到1986年70岁时退休。在其间经历的有文革的苦楚也有教学的乐趣,有在运动中受批判的委屈也有教学成功后的欣慰。
来师大一直教的是外国文学,主讲俄罗斯和苏联文学。我不会俄文,就不像读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的作品那样能从原文里迅速领略到精髓,这使我对自己所教授的专业只觉得前途无望。这个时候,也由于我的出身,每次运动受到批斗,情绪都很低落。教学生活中只有在郊区七个区县为中学教师授课,及在学校教授中文系著名的“八仙过海”课,方使我十分快乐。
文革之后我要求调到古典文学组,开始教授古典文学。这是我最擅长,也是最乐意向学生传授的。我教授古典诗词最大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让学生领略诗词真正的内涵,而并不是要把我的思想加注给学生。我想,我教书这么多年来在这一点上无愧于我心。
1951年我在天津津沽大学教书,当时党接收了这个天主教兴办的大学,改名为师范大学时,我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的党委书记王金鼎同志希望我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作为入党的阶梯。于是,我成为了民盟成员,积极地参政议政,曾在全国土改运动中去西南参加土改工作,以后在民盟市委和中央先后得到民盟领导、共产党员胡愈之,萨空了,王建,李文宜等同志的热心帮助,一直未改初衷,希望早晚能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得到落实,我感到欢欣鼓舞,再次申请加入共产党。
退休时,我的入党申请成了泡影,这曾一度使我灰心,也很不理解,但在当时总支龙德寿、党委浦安修同志却叫我不要灰心,应该继续争取。我想就从身边的小事做起,退休后继续在社会上讲学。我在国务院宿舍住了十几年,九十岁仍在这院里教宋词、红楼梦,邻居中大多数为老党员。有一次林伯渠的女儿送给我一本书,我为林伯渠女儿的事迹大为感动,觉得自己做得太不够了。后来街道居委会的党支部找我谈话:“您还想入党吗?您写份入党申请书吧!”去年师大给我过了90岁生日,我激动万分,心中的委屈一扫而光,并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今年6月27日上午,北师大文学院分党委退休教师党支部在励耘学术报告厅举行党员发展会,正式宣布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鲜红的党旗下,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噙着热泪宣读了我的入党志愿书。那一刻,在师大经历的点点滴滴在眼前如电影一般匆匆掠过,曾经对它的抱怨,曾经对它的不解,一瞬间都化为乌有,留下的只有难以言说的感激与感动!
悠然安享晚年时光
离开师大之后,我的心并不能真的离开我为之着迷和欢喜的课堂。退休后的十年,我应不同的学校之邀,仍然在外面四处讲学,只要走上讲台,我就觉得浑身又在散发着活力,洋溢着激情。也正是我的侃侃而谈使课堂的气氛甚为活跃,我一直被我的学生喜欢着,这给了我更多的动力。我在每次上课之前都仔细地备课,一个字一个字地做好笔记。
我80岁时,母亲生病入院,我辞去外面所有的事务,专心陪在母亲身边,直到她离开人世。母亲的一生和我患难与共,这些每一点每一滴都牢记在我心头。母亲离开之后,我的生活更加静谧了。我开始在我所在的大院给退休老人讲课。大家还都爱听我讲呢,讲完宋词后他们邀着我讲《红楼梦》,《红楼梦》结束后,又要邀我讲唐诗了。在大院的活动中心里,居委会协助我办起了讲课班,来听课的有林伯渠的女儿,有俞平伯的女儿……每周二的上午,他们都早早地坐在教室里,有书法特别好的人会事先给我在黑板上写好板书,有居委会的负责人把我的讲义打印出来分给学生。我的课是流动的,大家可以随自己的时间来听课,这样仍然有三十多位老人几乎成为了我的固定学员。今年年初,他们把我平日讲课拍下的照片做成了07年的日历送给了我,我寄了一本给我远在美国的大儿子。我抚摩着这情谊凝结的小册子,寥寥几页,却是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生耕耘的结晶,这是用任何金钱都换不来的啊!
每天早上,透过窗帘天空已经露出光亮,我便早早起来了。早上的空气清新,生活也充满着淡定自若的闲暇。孩子们忙着各自的事业,都不在身边,只有我和老伴伴随着满屋似飘有清香的照片和书籍悠闲度日。我打开电视机,调到央视四台,收听早间新闻。老伴则拿出报纸开始晨读。关心政治,了解时事这已经成为我们两个老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听着电视机里主播清脆的播报,我开始准备早饭。一杯牛奶,几个煮鸡蛋,几片烤面包,很容易也很简单。虽然家里每天都有小阿姨来打点,但我仍然会自己动手做点活。冲一杯牛奶,加热晚饭,有客人来了倒上一杯茶水……
如今,我还有勇气教我从来没有教过的《红楼梦》,只要学生说我教得好,我就敢教。我的三个孩子都对我好,大儿子仍在国外,小儿子每周会过来看我一次,女儿已退休,平时照顾我的饮食和购买衣物。老伴和我白头偕老,我的朋友和同学也都多极了,我想我最有福气的就是找到了一条教书的路——生病时有已经做了医生的学生照料我,过节时有各地的祝愿不断传来;“桃李满天下”,这就是我一生的见证,也是我幸福的见证!
(三)教育漫谈
1939年我开始在南开中学教书。头一回站在讲台上,我就爱上了教书这个职业,我希望我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很爱国,我觉得我也很适合做教师。我一看到孩子们那天真的眼神和对知识的如饥似渴,就对他们爱得不得了。今天,我对教育和做人的所有经验和感触,都是从那时开始一点点地积累的。
教书的乐趣
我教授的是古典诗词,拿到诗词,我就像沐浴在温暖的海洋里似的,沉醉在诗词丰富的艺术气氛里。要讲苏东坡之前,我可就坐不住了,走到哪里想的都是苏东坡。我不是纯粹地看书,人家怎么说我就跟着怎么说。我要自己理解,我要先把词会得很透很透找自己的心得,然后再在讲台上讲给大家听。我教书也不是要大家夸我教得如何好,而是希望通过我的教授使学生喜欢这首诗或这首词,要把眼光带到作者的境界,心领神会。这一招是当年在燕京大学顾随先生教我的,我就是学着他的。如今我的师妹叶嘉莹,发挥得更好。
我讲杜甫诗沉郁,那它沉郁在哪里;我讲李白诗豪放,那它豪放又在哪里。我不喜欢学生把我说的一字不漏地记在本子上,然后考前一背,拿个高分,过后别人一问又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想做的是寓教人于教书之中,在纯粹的艺术教授中融入教人的道理。这样我的课堂才会生动,情绪才能饱满,学生们才能感受到这种气氛一并被调动起来。我也必须让自己走得正,如果我走得不正,我怎么教人啊。也正是这样,来听我上课的学生们大部分都很喜欢我。有当年的学生现在来看我,提到我讲外国文学时的场景,就会问我:“您那时是怎么讲的啊,可让我们都感动得哭了。”我听着就笑,我教人多半就是要教人感动。我想,人要有一个人生观,师大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真是说到我的心里去了。我从来就不觉得教书是一回事,教人是另一回事。站在学生面前,用文学把你的感情表达出来,他们不喜欢你才怪呢!
教与学的互动
我不是学师范出身,但我就是爱教书。和教书相比,坐办公室的人面对的是一件工作,一道政策,一条纪律。而做老师的,却是直接面对人,面对的是对你满脸期盼的学生。你的一言一行都有他们给你打分,你的一举一动都有他们给出评价。你做得好与不好,都有可能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所以面对学生既要高兴,也要小心;既要放松,也要谨慎。人活在世界上,无非两个字,一个教,一个学。现在有人一问,“你是做什么的呀?”只要我回答是教书的,立刻对方就会说,“那你有寒暑假吧。”好像当老师就是为了寒暑假有空一样。如果教师一旦是为了自己的轻闲而忽视了做教师的意义,那就不容易教好学生了。因为老师是要与时俱进的。你不跟进知识,学生就会想,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啊。我在黑板上的板书写得不好,学生就会说,老师你这写的是什么,我不认识啊。学生都这样说了,我就只得快点去学啊。当老师的可以有错,但如果老有错怎么行啊?说服不了学生,又怎么能让他认真跟着我学习呢。
所以,教书是活生生的,当老师也必须特别努力。不能小看那些孩子们,他们可聪明着呢,现在很多家长都不知道,对孩子耳提面命的,把嚼烂的东西反复拿出来说,这可让孩子们不喜欢呢。当年我在南开中学实验班上课,规定我必须全英文讲课,最开始孩子们不是特别懂。我记得有一次我指着门说:“Please close the door。”一个孩子就似懂非懂地走到门那边把门关上了。我竖起大拇指笑着对他说:“Good!”得到鼓励,他立刻高兴起来,知道自己答对了。我真是爱他们极了,他们也爱我。每次一提出什么问题,他们个个举起小手争着回答,课堂气氛特别活跃。到现在当年这些孩子们都忘不了我,有人听他们英文讲得好,还问他们,教英文的老师是不是外国学校毕业的。
我老了,教书的时间一长,就搞不清楚谁是老师谁是学生了。现在遇到什么问题我都会打电话给我的学生于翠玲,着急地问她我该怎么办啊。她就具体地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怎么办。人活着就是这样啊,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是轮到我向学生请教了。
中西教育之异
我从前的一个学生到美国考察去了,回来跟我说,我们比美国差多了,以前只是觉得我们国家的工科比美国的差,现在发现文科也不如美国的了。我就批评他说,我们国家的文化怎么会差呢,我们的历史多悠久,美国的历史才有多少年,你觉得我们比他们差,这只是因为我们两国的教育方式不一样啊。
我哥哥当年读的牛津大学、我同学读的大学、我老伴读的加州理工大学等好几所外国知名大学我都去看过,发现它们和我们的大学确实不一样。就说苏格拉底,他的哲学怎么好啊,怎么到现在都被人津津乐道,那就是因为他的哲学是讨论出来的,在讨论中,也分不清苏格拉底到底是老师还是学生了,这就是最高的境界,教与学达到了互动。咱们的《三字经》里还在说“教不严,师之惰”,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老师严厉地坐在讲台上,学生在下面不敢说一句话,这样怎么能教出好学生来?怎么能有更高的成就?所以很多人就说,在中国拿高分的未必是好学生。多抽点时间读点自己感兴趣的书的人肯定比那些死读书的人棒。
我这一辈子关于学生、关于教书的话很多,一说起来就像合不拢的闸,哗哗往外流。这些年过去了,当年的学生也都打造了各自的一番事业,有的已经去世,有的还在继续工作,有的也和我一样退休过着悠静的生活,如今白发苍苍地聚到一起来时,还会有人说:“杨先生,再给我们来段宋词吧。”我一拍板说:“好!”于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首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又把我们带回到了当年激情昂扬的课堂……
(四)师生同门情
我爱我的专业,主要就是因为我听了顾随先生的课堂讲学。我20岁就在燕京大学听顾先生的课,那时候燕京大学有顾先生来讲课可是轰动了,可一到报名,就是登记选课的时候,我们中文系只有一张单子,不许超过50人,超过50人屋子就搁不下了。但是各系的人,骑车的、走路的,都往中文系里挤。没有选上课的也站在墙边、讲台底下听。为什么这么热闹?那是因为大家都喜欢听顾先生的课。
顾先生本身是个诗人,又是一个学者。他是在老家念的中文,到北京大学念的外文。从“五四”以后教学生,先教中学,再教大学。他教课就是把自己整个儿教给学生。他来上课,没有师道尊严的样子,也没有架子,对学生就像跟朋友一样什么都说,把自己整个地剖析给了学生。他自己有哪点不好,有什么缺点,他都说,像鲁迅一样,怎么想的就怎么教。他喜欢极了那些唐诗宋词,喜欢的时候就朗诵起来,我们也听得如痴如醉,都不用再讲了。然后,他会说他的体会。他哪里是在讲诗呢,他是在讲人生,讲怎么做人!他一会儿讲外文,一会儿讲古文,他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一会儿又转到京戏上去了。听他讲我们全都陶醉,思想不敢开一点小差儿,怕记漏了。课上先生讲到俄国有位作家安德列耶夫,我就下课赶快到图书馆把安德列耶夫的书找到;先生讲词,讲到这儿,好了,我就到图书馆把以前的著作都看了个遍。我那时就是这样念书。
我从二年级上顾随先生的词曲课,学习填词,得到了顾先生的赏识。但是我从来不敢登门造谒,甚至不敢到教员休息室单独求教。“七七”事变后,先生老了许多,他身体不好,坐骨神经痛,上课时穿着棉袍子,夹着椅垫子,进了课堂,放下书包,抬头用温和的目光扫视我们一遍,再从书包中拿出经他批改的我们的上周作业,往桌的右角一放,然后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他昨夜不眠时作的词,开始娓娓地谈论起来。待读到一首宋词时,兴致全来了,目光炯炯,语句有声,一片神往,旁征博引,把他的心、神、学问、灵魂全交给我们了。此时他的课更多的是弦外之音,常自称是弱者,以自嘲掩饰痛苦,其实在我们看来他才是真正的清醒者和勇者。批改学生的词,更便于他激励同学。我曾写过这些词句:“相期相望,重山重水,渐行渐远。”他给我密密麻麻画了许多圈圈,却没有一句评语,但我也能心领神会。
我离开燕京大学的时候,到顾先生家去了一趟。这是我第一次到顾先生家,我告诉他,我去内地,我要走了。顾先生鼓励我:“走吧,能走就走吧!”我走了,到了内地,无时不想念我的老师。我教书了,一教就是八年。我那时才22岁,不是太会教,怎么办呢?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我想,我模仿!模仿谁呀?只有模仿顾先生。他的学问我没有,他的那些本事我全没有,可是我有一点,就是他的教学态度。他拿学生当朋友,非常平等,不讲师道尊严——我这么讲了,你接受,那好极了;你不能接受,我也不叹一口气;你用功了,我看到了,你不接受,我也无可奈何。所以我就把这种态度给学生讲了,我教书不凶的,中学生都很喜欢我,当时我不知道。一直到后来,我80多岁了,他们都70多岁了,他们拿出来从前的笔记本,说那时候你讲的什么内容,你说的话,你给我们改的诗,我们现在还记得……
但是说起来很惭愧,顾先生门下的学生很多,但是我们却一直没有为顾先生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直到我的同门,比我低九届,旅居在加拿大的叶嘉莹上世纪九十年代两次回国,联系了很多顾先生的学生和有关单位,收集了顾先生的作品,并为顾先生举办了百年诞辰纪念会,我们才重新聚首,对先师诉说多年来我们对他的怀念与敬重。
说起我的同门叶嘉莹女士,如今已在国内外有一定的知名度。她依然保留着当年在顾先生的课上的笔记。在顾先生的百年诞辰会上,她激动地流下眼泪,说有今天的教书成就,那是得到顾先生的真传;有今天对人生的透彻感悟,也是缘自顾先生的谆谆教诲!
我是80多岁才认识叶嘉莹的,她回国后来找我,说是顾先生的学生。我们一聊天,顿时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当年顾先生在燕京大学教课,后来就转到了辅仁大学,叶嘉莹是当时辅仁大学的学生,所以有幸成为顾先生的门下。她那次回国,除了到很多大学讲学,就是要筹备顾先生的百年诞辰会。我比较了解国内的情况,就介绍她去找顾先生的其他学生。
叶嘉莹说一定要为顾先生做一点事情。1997年,由她捐赠,以顾先生的别号“驼庵”命名在南开大学设立了“叶氏驼庵奖学金”。叶嘉莹从教五十多年,对古典文学教育情有独钟,她用半生的积蓄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设立了这笔奖学金来鼓励学生从事古典文学方面的学习与研究。这笔奖学金的设立同时也是为纪念顾随先生,有师恩难忘的意思。
叶嘉莹虽然在教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她的人生路走得非常崎岖和坎坷。她给我看过很多她写的文章,我对她万分同情,在人生道路上,我比她幸福,但是说起她的创作和教授的成就,我真是自愧不如,十分地佩服她。我们是同门姐妹,我比她差多了。现在她又回到加拿大去了,我们也经常通信联系。她走之前,给我留下了当年她在顾先生课堂上的笔记,我捧着这珍贵的笔记爱不释手,同时,我和叶嘉莹心里那份感谢恩师之情也更深更浓了……
(五)我的哥哥杨宪益
我的哥哥杨宪益一生翻译过上百本中国著名文学作品,从希腊文、德、法、英文中译过荷马史诗《奥德修记》、《罗兰之歌》、《萧伯纳戏剧集》等,英译的中文作品包括《史记》、《资治通鉴》、《楚辞》、《长生殿》、《牡丹亭》、《唐宋诗歌散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鲁迅全集》等百余种。这其中有他自己喜欢的,也有他不喜欢的。他曾经做过《中国文学》的主编,也曾经首次出版了一套《熊猫丛书》在外国发行,深得很多人的喜欢。哥哥也喜欢写诗,著有诗歌集《银翘集》。
叛逆的性格
20世纪初我们是典型的封建大家庭,清朝灭亡之后,我们家也算是没落的贵族了。1919年父亲去世,留下的仍然是一个庞大的家族。父亲有三位夫人,我的母亲位居第二。但是家里的下一辈只有我哥哥这么一个儿子,所以我们都是拿他当宝贝,从小他就是我们的主人,家里的一切将来也都要由他继承。从读书开始,家里就专门请来两位先生教他,一位专门教英文,一位专门教中文,而我和姐姐妹妹们就和其他普通孩子一样去念小学和中学。所以哥哥的英文很好,典型的英国音。我的英文是在美国的教会学校学的,很明显的一口美国音,后来我们开玩笑,他说他不喜欢美国,我就说,我不喜欢英国。
我和哥哥的感情一直很好,从读初中开始我们就是同一个年级,我在教会办的女子学校读书,他上的是新华中学。哥哥读书时非常聪明,他都已经能把十三经背得滚瓜烂熟时,我连四书五经还没有读会。但是哥哥平时在学校里唱的歌和玩的游戏却都是我在家里教的,这方面他还得向我请教呢。他初中时就琢磨着写章回体小说了,写的东西也都是我用毛笔帮他抄下来。
毕业之后哥哥就随他的老师去了英国伦敦。走之前我们的嫡母希望他留下来继承家产,但是哥哥还是坚持要出去。像我们那样的封建大家庭里长大的孩子,都很叛逆,在家里受到很多管束,总想出去寻找自由。哥哥就是这样,去英国时他特别高兴,心想终于摆脱了家庭。
独特的选择
哥哥后来考取了牛津大学,在那里学习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并且拿到两个硕士学位。当时中国已经处于一片水深火热之中,抗战的热浪一阵高过一阵,哥哥也在英国偷偷印刷一本叫做《抗战》的小册子,宣传抗日。哥哥本来可以继续攻读博士的,但是他放弃了,他说起理由来很奇特,他说英国的博士都要戴着博士帽向英皇的肖像下跪,我堂堂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向他们下跪。
哥哥在英国很少来信,有时来信内容也是少之又少,我清楚记得有一次他的信里只有一句话,就是:“NO NEWS IS GOOD NEWS。”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哥哥有的来信也会和我谈起他在欧洲生活的所见所闻。但是,哥哥从来没有提到他交女朋友的事。直到有一次,他给我来了厚厚一札信,我非常惊讶,打开来一看,除了信件还有一个英国女孩的照片。哥哥说这个女孩非常好,你看了也会喜欢的。在当时我们那样的家庭,母亲是不会同意哥哥娶一个外国女孩的,于是,哥哥就要我给母亲做工作。我把信仔仔细细地读过之后,对母亲说了。然后我慎重地给我哥哥的这个女朋友——Gladys Margaret Tayler(中文名字戴乃迭),写了一封信,不久后就收到了她的回信。她在回信里也直言对我哥哥的感情,并说自己也是出生在中国,父亲曾是燕京大学的教授。
母亲的思想工作我来做,最后母亲同意了,但是坚持在以后的人生里要和我生活在一起。我去了重庆之后,我的朋友罗霈霖也来重庆做地下工作,再后来我的哥哥和他的女朋友来了,于是我们就在重庆一起结了婚,这在当时叫双婚。我的这位嫂子最开始中文不是特别好,和我母亲的交流都是由我从中做翻译。在这段时间我也有机会和我的嫂子接触,发现她真的如我哥哥所说特别好,而且她说话很直接干脆,有时比我还率真。
翻译的乐趣
哥哥也热爱历史,但是他是为了妻子的前途才做翻译工作的。1943年起他供职于重庆北碚国立编译馆,开始了翻译生涯。1952年他调到北京外文出版社(今外文局),后任《中国文学》主编。在他的翻译生涯中,他的夫人,也就是我的嫂子一直都是和他并肩作战,谈到此也有很多趣事。
哥哥做翻译,最大的特点是快,他打字都是用一个手指头在键盘上敲。他翻译“鲁迅小说”到《红楼梦》都是左手拿着书,眼睛盯着书,右手的食指就在键盘上飞快地敲。一个多星期就完成了,我这一辈子没见过一个人有他这么快。他做完就把手稿交给嫂子,嫂子坐在旁边一张小桌子旁,拿起他的稿子一遍遍地审,认真地修改。当时研究《红楼梦》的吴世昌看到英文手稿后觉得有些地方不妥当,就会打电话来直接找我的嫂子,嫂子认真听取他的意见,再做修改。可以说虽然哥哥是搞翻译的,但是他的翻译的所有善后工作都是由嫂子来做。人们称他们为夫妇翻译家,也正是他们俩的鼎力合作,工作效率才非常高。这在文艺界已经成为了一段佳话。
哥哥和嫂子后来也搬回了北京。我们经常去他家,哥哥虽然英文很好,但是从不随便在别人面前带有洋腔,有人说他是英国绅士,他也不放在心上。他的学问从不挂在脸上,也不挂在嘴上。嫂子的中文越说越好,他们的三个孩子虽然听得懂父母的话,但是却不会说英文。
情痴的一生
哥哥和嫂子一辈子特别要好,工作上一起合作,生活上相互帮助。嫂子去世后,他就没有再翻译过东西,他说他现在没有了帮手,不能再做翻译了。他散尽了自己收藏的作品,只留下和嫂子的照片作为怀念。
哥哥这一生有两个遗憾:其一,是他懂拉丁文,希腊文学也好,却没有在中国充分用上;其二,他一心想研究中国历史,却做了一辈子的翻译工作。说起其中的原委,这便是他的夫人。他要和夫人一起合作,夫人的事业才能有更大的成就。只要她做得好,他也就觉得非常好了。
哥哥的一生用情至深,他最喜欢别人表扬他的夫人。有人说:没有你的夫人,你就翻译不成,他听到这样的话是最高兴的了。
(六)烽火中的纯情
“我这辈子就她一个女朋友,她这辈子也就我一个男朋友。”这是罗霈霖最喜欢对别人说的一句话。别人开玩笑地说:那你可真亏了啊,他就望着我傻傻地笑……
执子之手
我们那个年代,烽火四起,硝烟弥漫,谈爱情真是太奢侈。如果一定要说说我和罗霈霖的爱情,那么我的理解就是,我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对很多事情有共同的看法,这种共同的价值观促使了我们的结合。对此我深有感触,我的两个孙女都结婚了,又离婚了,我也知道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婚姻失败在什么地方,那就是一开始时就不慎重,不去互相了解。
我和罗霈霖是通过我堂哥认识的,我们这些“少爷小姐”经常在一起玩,一起讨论问题。日军侵华时,很多人仍然有心情去看电影,去听唱片,而我却想这样玩真是太没有意义了,我们也应该去投身抗战,为国家出一份力。罗霈霖和我的想法一样,我们那时经常互相通信,聊一些国家大事,罗霈霖家也是当时天津的大户,在我们这群人中只有他最可怜了,读初中时婚姻就被家里包办了。他的几个姐姐也是早早地就订了婚。互相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模样,出身如何。我觉得他特别地倒霉,不是爱情而是同情。在知识和爱好上他胜我一筹,我有点佩服他。罗霈霖很反对这种包办婚姻,读大学时就开始找律师要解除这种婚姻关系。当时他告诉了我,我给他回信,坚决支持他反击这种封建思想。那时有人说我是为了占他女朋友这个位置才支持他取消从前的婚姻,其实我是觉得这种包办婚姻就是不应该。那时我们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读鲁迅的文章也读得特别多,我们两个都喜欢鲁迅,就是到了现在,碰到填表,一说最佩服的人是谁,我们两个就会不约而同地填“鲁迅”。
罗霈霖有一点特别好,就是做完一件事再做另一件事,他那边的包办婚姻还没有解除, 他就从来不和我谈感情,我们之间通信,也不涉及这些。他总是觉得要把那边的事情解决了才和我开始。罗霈霖送给我一本纳兰词,那是我的第一本词,因为是他送我的,我就念得比较多,后来我到大学里就开始学作词,结果作的词和纳兰词一个风格了,老师告诉了我,我大为吃惊。
抗战期间罗霈霖去了延安,去之前我也没有说什么,我就想他应该做他想做的事,我不能成为他的负担。我念了一年半研究生后和母亲去了重庆。不久,他受党的派遣从延安到重庆搞地下工作,在那里成立了一个青年科学技术会,宣传让更多人团结起来。我母亲在我的影响下,拿出四万元来资助他们,自己仅留下两万元维持家用。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紧张,我们为了掩饰身份,就举行了双婚:我哥哥嫂子和我们二人,证婚人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的张伯苓。
婚后的生活对我来说很紧张。因为他的工作身份,经常要出去办事,却不能让我知道。他每次出去我都提心吊胆的,平安回来我就悄悄地舒一口气。我也和他说,不管你出去做什么,只要能平安回来,我就高兴。
患难真情
解放后,党让他去美国继续深造。我支持他出国,他曾是去过延安的人,出国并不是为了镀金。可是他一出国我就又是一个人了,要照顾我的母亲,还要抚养两个孩子。但我仍然坚定的是,我这一辈子不会成为他的负担,永远支持他做他喜欢的事情。
在美国读了一年半,他就抗美援朝去了。他情愿放弃博士学位,要回中国,但最终他还是提前毕业,得了只给学习成绩好的人的“金钥匙”。回国之后,组织把他调到了北京,进了电信工业局,他又被提为两院院士,我们家也搬到了北京。在北京,他也是经常出差。有一次出差回来,收到一封匿名信,大致是说我现在有多少求婚者,有多少人喜欢我,但是他看了完全不理会。我想这也是延续在我们两人之间最重要的一点:信任。我充分信任他,他也充分信任我,任何流言蜚语都不会对我们造成损伤。
然而比起抗战时的艰苦,出差时的分离,更严峻的时候来到了。文革期间受到各自所在单位的批斗,我们被隔离了。在被隔离的那段日子,有人来问我,还要不要和罗霈霖在一起,我每次都坚定地回答:要!在那个时代有很多夫妻就是在残酷的批斗中退缩而抛弃了彼此,而我一直坚定我不会远离他,他也不会远离我。我那时总想,罗霈霖是党员,曾经去过延安,也是受党的指挥去重庆做地下工作,不管他的出身如何,他一直都是爱党爱国的,他肯定会没事的。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患难中更坚固了感情,我也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患难见真情。人这一辈子不容易,正是一起经历过那么多事情,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与子偕老
我和罗霈霖的性格反差很大。他是学工科的,平时寡言少语,做事说话都非常谨慎。我是学文的,一说话就像打开了话匣子没个停。我就把我们比喻成两个坏了的水笼头,把我拧开,水就流个没停,关都关不住;把他一拧开,怎么都不出水,但是一关上,水又忽然流出来了。罗霈霖也有点奇特,博士毕业时大家都戴着博士帽,但是就他不戴,我觉得遗憾极了,他倒觉得没什么。
早些年,晚上忙完一天的工作,我喜欢和我母亲还有孩子们看看电视,但罗霈霖不喜欢这些,言语也不多,回到自己的工作室忙他的事情去了。但是我知道他对我的心是真诚的,有时我们也因为性格不合吵吵小架,但是吵完马上就过去了。一想到他那么好,那么辛苦,我就不忍心和他吵架了。
已经91岁了,但我还戴着罗霈霖送给我的戒指。说起这戒指,还有段小故事。我们刚结婚时,罗霈霖托朋友在香港买了两个金戒指,他一个,我一个。后来我瘦了一些,戒指就显得大了,有一次送我舅舅去乘车,给弄丢了。罗霈霖看见我的戒指丢了,觉得他戴着那个也没什么意思,就把那个拿去卖了钱,补贴家用了。可是罗霈霖知道我喜欢首饰,后来手头宽裕些了,在钻石婚前就给我买一个钻石戒指,很时尚,像现在刚结婚的小夫妻戴的。我现在是每天都戴着,抚摸着它,内心就充满了甜蜜。
我们两个在一起没有怎么玩过,年轻时都很忙,现在都老了倒天天待在一起了。偶尔吵个小架,他也不和我计较。每天下午我们都喝下午茶,他为我冲上一杯咖啡,切上一块点心,便凝固住了我们相濡以沫的一生最精彩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