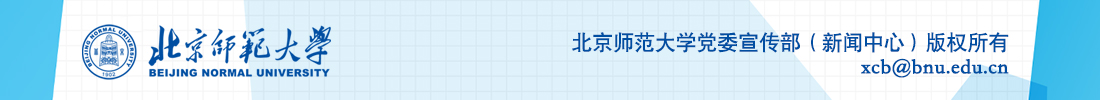编者按:在战火纷飞的动荡年月,他坚持读书,在破祠堂改造的教室中初尝数学的乐趣;在教学科研的钻研中,他对代数环上的线性群情有独钟;他研究的“无穷质点马尔可夫过程与Q过程”荣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他直逼教改:“亮剑”高考与奥数;他说“真正的数学与大众所知道的那个概念相去甚远”……他,就是严士健———在代数、数论和概率论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及教学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数学家、教育家。从本期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严先生的“数字城堡”,探寻严先生与数字相伴、与教育结缘的人生奥秘。
(一) 动荡年月读书难

我的中小学时代都是在抗战时期度过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前,我在武汉实验小学读书,光一年级就读了三个学期。为什么呢?当时的小学是寒暑假都招生的。我上小学时还不到五岁,上学第一天下第一节课,大家都出来玩,我就以为没课了、放学了,我就回家玩了,结果一学期就留级了。后来我又念了一年,也就是两个学期,这回及格了。之后,家里认为我应该念个好学校,就把我送去了武汉的实验小学。
自实验小学开始,我念书就比较认真了,不再像小时候有点糊里糊涂。然而,两年之后,我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那是1936年5月,我只有七岁。
小学期间,“卢沟桥事件”发生了。那时候的我对政治上面的风云变幻自然是非常懵懂,但我记得,几乎所有的电台、街上的音乐都在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同时到处都在唱救亡歌曲,比如《大刀进行曲》,抗日的气氛非常浓。在县城里,有抗日宣传队的演出,演到日本人的时候,下面真有人往上跩石头。
有一个画面让我印象深刻———在岳麓书院的湖边,有一个阅览厅,阅览厅的底边与湖边的小坡之间有一个小角度可供容身。我们就窝在这个小空间里,看着战争就在我们身边随时发生。夜晚,日本人的飞机亮着灯飞,我们的高射炮,实际是高射机枪,一个接一个的炮弹打上去,有时候没打着,如果打着了,飞机就会起火,这一切在阅览厅下面的我们都看得见。如果还有什么在我的记忆里,那就是从安徽一带逃荒过来的百姓,挑着担子、推着小车……这一切,就像如今电影里面演得那样,然而却都是真实甚至恓惶的现实。
后来,武汉失守,但是当时的军队也是拼命了,打得很厉害。怎么能证明呢?有一个小细节,就是1938年我们上学时,使用的铜盆都是打完仗后用捡的子弹壳做的。由于战争,读书也是时断时续,1938~1939年我又念了两年私塾,才在我们那里的一个镇上了高中。那时的高中叫做联中,是在那个战区里头,湖北,安徽,河南几个省的联合中学。我初中是在黄冈县立初中就读。那个学校始业在冬天,1944年底初中毕业。1945年上高中,是秋季开始。1944年冬天到1945年夏天,在家里。高一上学期在山里头,下学期到了下巴河;1946年冬天到1947年春天,我到了武昌高中,是湖北省立中学,虽然不算最好的学校,但已经好很多了。
当时虽然什么都匮乏,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书。提起数学,初中时候我就做了不少题,像《800难题解》,数学方面的训练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训练印象特别深,我们学几何是先学一些实际例子,然后再学证明。开始学论证的时候不知道到什么叫证明,要证明到什么程度。刚学完等腰三角形底角相等,老师让我们证等边三角形的三个内角相等。老师大概想考考我们,就说我去剃头了,结果我们班就“吵”开了,其实就是争论什么是证明;拐七扭八也算证出来了。老师回来了一讲:等腰三角形两个底边相等,两个底角相等;等边三角形是等腰三角形,这两个底角相等,那两个底角也相等;因此,三个内角相等。啊!证明就是这个道理。
还有一个学习的细节我印象挺深。大概是初中,老师讲平均速度和瞬时速度。当时我们就琢磨,什么叫平均呢?最后我们居然悟出来,所谓每秒5米的意思就是,按照5米这个快慢走。现在想想,觉得当时我们这一群爱思考的孩子真可爱。
这些学习经历,相对于现在的生活来说,是历经了一些磨炼。与老百姓受的很多苦难来比,不算什么。在我看来,参加学校劳动对我们是有锻炼的。我们需要砍柴,然后木柴需要我们从山里搬到几十里地之外的学校,都是山路。当时还小,真是咬着牙坚持再坚持。
那个时候,吃饭没有菜,一年365天,饭是糙米饭,去壳不去糠,菜是豌豆,先干焯一下,趁热把水一倒,煮开了,几个人蹲在地下吃。粮食经常不够吃,只能抢着吃,开始是盛一小碗,吃第二碗时,就知道给自己盛尖尖的一碗,真怕饿肚子。晚上睡觉就在祠堂睡通铺,一个人一尺一寸宽,每人只能侧着睡,晚上你要起来小便,回来就没地方了,必须挤进去,这个体验我现在还历历在目。
那个时候,学数理化最痛苦的就是书少,而且物理和化学的实验都没有器材,这种匮乏感反而激励了我特别想上大学的心愿。当时高考都是各个学校自己命题,我是想去清华大学的电力系读书。其实我还想念哲学系,原因就是曾经念私塾,看过一些孔孟的书,对他们的思想有感觉。那当时我怎么到了北师大呢?因为最后一年我生病了,当时2个师大保送生的名额,是教育部分配来的。其实我们的学校不算是非常好的学校,但是它采取了大量的淘汰,留下来已经不容易了。我们班有60来人,实际剩下15人,后来又来了15人,最后毕业是30人。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就对我说,你还是尽力考吧,北师大是不错的学校,考得好就上,考不上就保送。结果,我给考过了,所以就上了北师大。(采访整理:李仲来 张蔚)
(二) 大学时代研究出的“世界第一”

在大学里,让我印象深刻的老师很多。当时数学系的助教老师中有一位是袁兆鼎,由于他当时还没有成家,成天和我们在一起,给我们推荐学界前沿的书籍,比如范德瓦尔登的《近世代数学》。通过他,我认识了王世强老师。王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近世代数,你要研究一个系统的话,首先要把它的结构搞清楚。与他们在一起我特别爱问专业问题,所以获益良多。
刚解放时,游行特多,有时还能听到枪炮声。当时赵慈庚老师给我们上微积分,有人劝他为了安全别上了,但是赵老师不为所动,在课堂上一丝不苟的讲解,我们也认真的听讲。这一经历非常可贵,不仅让我们没有荒废学业,而且学会了如何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那个时候我的兴趣在函数论,经常在口袋里装着一本很小的《复变函数论》,休息的时候就拿出来看。当时我们要做一些社会工作,比如给食堂师傅读报纸,即使这样,我还是抓紧时间念了一些书。
还有一位老师对我影响很大,是傅种孙。当时我们读大二,傅种孙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他受教育部的委托,举办了一期中学骨干教师训练班,为期一年。傅先生对训练班的学术水平十分重视,几乎遍请北大、清华以及来京出差的数学家讲演,前后二十多次。我每次讲演都听,从张禾瑞题为“几何作图不能问题”的讲演中悟到了代数可以解决几何问题;从程民德的讲演中知道了实数还需要构造;从陈民的讲演中了解到还有非欧几何学;苏步青讲微分几何,一开始就用到“张量”,虽然没听懂,但是我知道了向量以外还有张量,而且对微分几何有用……各种各样的讲演使我开阔了眼界,知道了数学知识像浩瀚的海洋,有无穷无尽的东西要学,这一下子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
1953年,华罗庚先生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举办《数论导引》讨论班,亲自讲授,系里同意我参加。那时交通很不方便,两小时的讨论班路上往返就要6小时。有几次到了数学所,因科学院的人去参加大会讨论班而暂停授课。华先生不忍让我白跑一趟,就单独教导我,如“念书不能贪多,不要和人比念书的数量,要真正读懂”等。华先生当时已是著名的数学家,但对青年人提出的问题很尊重。在一次讲课中,我发现华先生有一步推导过不去,当场提了出来,华先生经过思考,认为我说得对,就重新准备后讲了有关部分。华先生这一行动不仅促成了我勇于提问题的习惯,更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的治学态度。
在讨论班读《数论导引》中关于“整数矩阵”的内容时,我提出:用生成元表示一般正模方阵,除了书中的方式外还有另一种方式。华先生很重视这个问题,进一步提出:“既然有两种方法表示同一正模方阵,那就产生一系列的生成元恒等式,这些恒等式是否可约?能否把生成元的不可约恒等式全部找出来,成为模群的定义关系?”这个问题吸引了我,我研究了六七个月。除上课和三顿饭外,我每天从早8点到晚11点就是计算,简直算得入了迷。华先生在每星期见面时都要问我进展如何,而我的回答多是“还不行”,每每这时华先生便总是鼓劲。
有一次,我自认为做出来了,当时华先生正在开科学规划会,得知后立即安排我去会场作报告。可是,下午就要报告了,我中午却忽然发现推导有错误,华先生又为我临时取消了报告。这样的情况反复了三次,我心里真想打退堂鼓,觉得辛辛苦苦六七个月完全白费了。但华先生却用鼓励而热切的话语安慰我:“不要紧,咱们再想办法,失败是成功之母。”
虽然这个问题不得不暂时搁置一下,但是功夫没有白费,我已经把矩阵的性质了解得很透彻,恒等式也算得非常熟。当时万哲先告诉我已解决了“主左理想子环上线性群的自同构”问题。在这一信息的启发下,我进一步考虑“一般可换环上线性群的自同构”问题,把“平延生成的特殊线性群的自同构”问题解决了。这是“一般环上典型群自同构理论”在世界上的第一个研究成果,它比美国O’Meara学派的有关结果早发表9年,后来被美国的J.Pomfert及B.R.McDona1d等充分运用并给予高度评价。接着,我用同样的方法解决了“由平延生成的辛群的自同态”问题,完成了论文《可换整环上的线性群》。直到1980年代,美国著名数学家O’Meara来北京做报告时,还多次提到这以一方法,并说“看来环上辛群的自同构也是严士健最早做的”。
对于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1956年8月下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在显著位置作了如下报道:“解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数学论文宣读大会显示了中国数学研究的迅速发展”,“许多青年数学工作者提出的论文也表现了他们突出的数学方面的才能”,“老数学家在谈到王元、严士健、尹文霖、陈景润、谷超豪、夏道行、丁石孙等论文的时候,都认为这是中国数学界十分可喜的成绩”。同时由于教学成绩,在这一年我被评为“北京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环上的线性群”这一工作完成之时,华罗庚先生欣慰地说:“这真是平地拔葱!”并且希望我能到数学所来做他的研究生。我就问将来的毕业论文该怎么写,华先生说:“你这一篇就绝对够研究生论文水平,而且是优秀论文。”1957年,我做了华先生的研究生,和王元、陈景润等人成了朝夕相处的同学。正当我准备追随华先生在数论领域里纵横驰骋之时,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师大让我回校,我不得不终止了一年半的研究生学习,由此也改变了一生的研究方向。“大跃进”中华先生的压力也不小,后来得知我改研究概率论,华先生惋惜地说:“你在数论领域已经站在了世界的最前沿,而搞概率论却要从头开始!”
我对华先生的惋惜之情非常理解也饱含感恩,但是我并没有为改变研究方向而后悔。虽然那时在数论领域搞出了一点名堂,并不意味着后来能出多大的成果。而在概率论领域,我在北师大带出了一个团结拼搏的研究集体,在世界上也为中国占据了一席之地,同样是很欣慰的。不是有句老话嘛———功成何必在我! (采访整理:李仲来 张蔚)
(三) 不为人知的“数学”

我一直认为师大学子真正学完数学毕业后,不光要学会计算、概念清晰,对数学的本质也要有较深的理解。我国传统应试数学的重大弱点之一,就是只注意数学本身的习题解决,不注意数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的关系,结果使得数学处于和社会生活隔绝的状态。
于升学率的压力,中学的数学课大量做题,甚至将题目归纳成各种各样的题型,让学生进行大量的模仿和重复。这使得学生负担加重,优秀的学生对数学感到厌倦,吃力的学生对数学产生了恐惧心理,以至在课程学完以后大都远离数学。渐渐地,社会上对数学的作用就不大了解,甚至有一种神秘感,到最后形成了敬而远之的态度。由于数学的作用没有被理解,更没有被社会所接受,剩下的似乎只是学生们升学和取得学分的需要。
谈数学教育,首先要谈数学修养;然后是数学功底;再是对现代数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很好地谈数学教育。关于数学修养,我一直主张,高等教育的研究者要做一些初等教育的教学;教授初等教育的老师也要注意高等数学的发展。但是目前全国的现状都不容乐观,初等数学不了解高等数学,脱离现代数学,成了高考的工具;而高等数学的人,并未真正了解初等数学,变成了纯搞竞赛。我觉得应该从社会需求出发,学生学的数学知识能够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同时还要使学生学会数学的思考方法。
当时,我曾经提倡数学系的老师认真写一些外系使用的教材,主要指的是与数学有交叉的学科。我也热烈地鼓励老师去外系兼课,这样就可以把数学应用于其他学科,结合一个领域来研究些前沿问题。当然,也有老师不太认同,认为操作起来有困难。其实,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认识数学的问题。
现代数学在20世纪有了巨大发展,刻画和表达各种现象的数学方法空前得到发展,数学的各个分支之间的综合与相互渗透以及向各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渗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对社会的进步也起着空前的推动作用。随着计算机的飞速发展,数学与计算机技术的结合形成了所谓的“数学技术”。它们对高技术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以至有人说“高技术本质上是数学技术”。如果我们再不改革数学教育,就会影响今后几代人的现代科学文化素质,进而影响我国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是关乎国家民族兴衰成败的大事。
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一点就是数学的地位不一样。中国文化对数学重视不够。实际上,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数学在西方文化思想中心地位的话,我们就不可能了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类文明及人类的所有创造。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也用了数学思维,《资本论》的出发点是商品,抓住商品这样一个人们天天接触的东西,进行了深入分析演绎,抓住了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就仿佛有一个数学公式。
数学家库朗曾说过:“数学在培养人的素质方面有根本的作用。”前苏联数学家辛钦曾说过:“数学教学可以培养人正直与诚实的品质,可以培养人的顽强与勇气。”每每想到这些,我就认为数学教育值得好好反思。形式的计算演练有助于能力的培养,但无助于智慧的开发。
我坚信,数学对中国文化的复兴、对中国的现代化有根本性的带动作用。中华民族的强大不仅要靠文化,也要依靠数学。从西方的文艺复兴来看,西方现代的科技发展是从文艺复兴发展而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师范院校真应该把建立强大而为社会所知所用的数学学科当成一件大事。(采访整理:李仲来张蔚)
(四)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严先生(前排左二)与学生们
1976年后,我恢复了中断十年的概率统计“讨论班”,一方面学习十年间“随机过程”、“数理统计”在基础理论方面的新进展,一方面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新动向展开了调查研究。1977年,当我听闻“非平衡热力学与耗散结构(非平衡系统)理论”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后,便和李占柄合作对其中“Master方程”进行分析,明确提出了它赖以成立的概率假设,形成了一般的概率模型,并用“初等概率方法”严格地建立了“Master方程”的数学形式。文章发表后,受到欧美学者的重视,这是我们研究反应扩散过程的良好开端。
1978年,我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和进修教师,紧接着便和陈木法、丁万鼎、唐守正、刘秀芳等人投入到“无穷粒子马尔可夫过程”的“可逆性研究”,提出了一般模型,完整解决了“自旋及排它过程”的问题。因此,1985年获得了国家教委首届科技进步二等奖。1990年,国家为使数学在21世纪率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设立了“数学天元基金”。“粒子系统与随机场”成为天元基金重点项目,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2001年,北师大的概率论研究获得了国家“基金委”240万元的创新科研群体资助,在数学界,这是唯一被资助的项目。
科研的关键是人才,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我们花了很多工夫来发掘和培养人才有关。1965年,师大数学系的陈木法在“文革”中毕业,他实际只读了一年大学,离开学校后给我来信,希望继续学习概率论。我热心地替他买了一大批很有价值的参考书,帮助他制订计划,指导他读Loève的《概率论》,支持他在侯振挺指导下开展研究。“文革”后陈木法成为我的研究生,并在我的支持下出国进修。陈木法后来成为北师大培养出的第一位博士,在1986年被破格提拔为教授,1990年已是博士生导师。他获得过霍英东青年教师奖和基金,并在世界数学大会上做了长达45分钟的专题报告;2003年,陈木法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些成果都是非常难得的。
1978年,我开始招收研究生时,收到唐守正从延边森林调查大队写来的一封长信,叙说了他如何喜欢数学,如何在野外工作的间歇期间学习数理统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并将它用于林业统计。
但是他从大学学习以来,始终与正规的数学学习无缘,因而希望考取北师大的研究生,进一步学习数学。我为他学习数学的热情所感动,并且欣赏他头脑清晰,便招收了他。在唐守正获得硕士学位以后,我十分希望他能留校继续数学的深造,但未能如愿。于是,我就一方面鼓励他去林科院工作,可以发挥他的林业和数学的知识技能,同时积极争取研究生院同意他攻读在职博士生,这一想法得到了当时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王桂筠的破格同意。事有凑巧,在他刚刚获得博士学位之际,袁兆鼎教授获知有位加拿大教授需要聘请一位统计学的博士后,我又及时推荐了他。唐守正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二年,就被破格提拔为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如今已是中科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生命科学的重大项目“我国主要用材林生长模型、经营模型和优化控制”的主持人,林业科学院的首席科学家。
我的学生中,还有一位叫郑小谷。他1975年进入北师大数学系学习,1977年毕业后考中科院软件所的研究生,成绩没有达到录取标准。而我和王树人都认为他确有潜力,便向师大申请录取了他。现在他已在新西兰工作,是地震和气象统计预报方面的有影响的专家。入学的这件事儿,成了他们家一个善意的玩笑。郑小谷的妻子逗乐说:“你天天美什么呀?人家科学院都不要你哩。”郑小谷便理直气壮地回应说:“科学院不要,严先生要!”
或许是因为我在人才培养中做出了一些成绩,1989年北京市授予了我“劳动模范”的称号,鼓励我继续为人才们“好好劳动”。也是这一年,国家教委授予了我和陈木法及刘秀芳“普通高校教学成果国家级优秀奖”。 (采访整理:李仲来 张蔚)
(五)直逼教改:“亮剑”高考与奥数

■严先生在书房
我在中国数学会做副理事长8年,在教育工作委员会做了3届12年的主任。我一直觉得,数学要让老百姓了解,在平常要注意应用;后来,我更慢慢体会到数学在培养人的思维方面乃至意志与品格方面作用很大。
90年代初,我应邀赴广东参加座谈会,商量起草关于数学教育的若干建议,“高考”就是其中绕不过的话题,我们当时就认为老让学生埋头做题这种方式有问题。后来,张奠宙、苏式冬与我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国考试》与《数学通报》上,这篇文章引起了数学界与教育界的一些反响。我们三人还拜访了当时的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杨主任也赞成我们的说法,他认为“高考老是这样做题,是能力的异化”。再后来,我找到了数学系的毕业生任子朝,他支持我们出一些针对高考的应用题,提醒大家注意应用。我们就一年一年坚持出题,后来对高考出题的思路也有些影响,但并不起根本作用。
我做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时,还是普通高校数学与力学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教委高教司要进行面向21世纪的高校课程体系改革,邀请我参加会议发表意见。我在会上的发言依然强调的是“带有本质性的应用不能忽视”,后来我的发言发表在《数学通报》与《教材与教学研究》上。
制订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改革,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让我和张奠宙担任组长,主持数学课程标准的工作。我的认识中有一点最基本的:英美的教育理念值得学习,但是全盘吸收肯定不行。美国教育主要是受杜威的教育思想影响,其中强调学生和生活结合、主动学习和应用,这些方面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但是,“以生为本”,连教师的主导作用也不提,这是不行的。
改革高中课程标准的小组成员都是数学系出身,因此我们广泛征求了一些数学家的意见。专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四点:首先,要注重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包括知识的实际背景和来龙去脉,这样才能达到掌握数学知识;其次,要注意文理结合;再次,在数学思维上能够得到一些启发,数学思维还能应用到别的地方上去;最后,这个课程标准应体现多样性,掌握社会上对学生数学素养的不同层次的要求,制定不同的课时标准等。结果我们制定的很顺利,数学的高中课程标准在来年四月就出来了。其中,我们还加入了算法、统计等。为“教改”和高考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还有一个经常萦绕在我心头的问题就是“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数学奥林匹克是个好事,应该让学生去自然的学习和竞赛,而不是强化训练,这一点可以说数学界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我认为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总出一些偏题怪题,认为这就是数学,这样的想法并不可行。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都把精力集中在出偏题、怪题,的确数学建模的本领越来越高,但是实际上哪有那么多难题呢,这样便偏离了方向。这些竞赛的初衷都是好的,但是执行起来却经常变味。
对学数学的人来说,做做题很好,但是纯粹的训练解题技巧对数学没什么好处。后来我们想出一个办法,举办“中学数学应用知识竞赛”,强调数学的应用性以及解题的多元思维和方法,我们还坚持“不搞培训”,结果我们发现孩子们提的问题挺有意思,五花八门。当然,现在还是数学奥林匹克影响最大,不光是金牌吸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保送资格的获得。我曾提议,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结果不作为保送资格。结果有人戏谑说:“取消保送资格就没人来参加竞赛了。”
教育主要是要激发学习者的兴趣和创造力,应该让人收获一种获得知识的快乐,而不是像奥林匹克竞赛那样不停地训练和比赛,奥林匹克竞赛本身是一种比赛,一些训练是必要的,但是不能让学生想起来就紧张。同时,我认为,有竞赛的经历,对从事研究会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得奖并不是一个在学术或应用取得成果的指标,真正要进行科学研究,也不能以是否参加过模型竞赛为标准。真正去研究应用,要真正深入到实际,深入到专业,能真正知道怎么样提炼出模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竞赛的真正目的达到了。(全文完;采访整理/李仲来 张蔚)